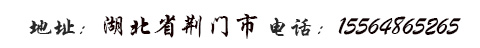谈书鉴画葫小乾坤大清代人物画中的葫芦
|
图1、清·冷枚《策蹇远游》,绢本设色,28.4x30.9厘米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、清·苏六朋《骑驴人物图》,纸本设色,x54厘米,澳门艺术博物馆藏 一 一老者头戴草帽,骑驴行于溪山,一书童着青衫,肩扛大葫芦,疾行追随其后。两人乃山间行旅,山势嶙峋,杨柳依依,旁则水流潺潺,野花盛开。这是清代康熙、雍正年间的宫廷画家冷枚在其《农家故事图册》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(图1)中描绘的山中一景。这本画册共计十二开,分别描写农家收获、儿童采果、塘边汲水、晴窗课读、雨窗对坐、月下听泉、策蹇远游、农闲时光、松下对饮、路遇樵夫、牧牛归来、山中隐士等十二个场景。前述骑驴远行者即为《策蹇远游》。很显然,书童所携带之葫芦,在画中主人方面,具有容器的功能,或盛水,或装酒。这种画中葫芦,在清代人物画中并不鲜见,甚至成为多数行旅类人物画的标准配饰。同样的画面也出现在清代中后期人物画家苏六朋(—年后)的《骑驴人物图》(澳门艺术博物馆藏)(图2)中。该画描绘的仍然是一老者骑行于驴背之上,一书童背着葫芦紧随其侧。画面除人物、毛驴外,无任何衬景。作者在画中有题词曰:“乱花飞絮,化作琼林玉树。驴背是何人,得了灞桥诗句。归去,归去,家在醉乡深处住”,似乎是以贾岛驴背吟诗的典故入画,刻划文人苦吟的故事。此处的葫芦,亦为容器之属。 图3、清·黄慎《牵车图》,绢本设色,24.8x24.5厘米,天津博物馆藏 图4、清·居廉《牵车图》团扇,绢本设色,直径26.5厘米,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具有同样功能的葫芦也出现在“扬州画派”画家黄慎(—)和晚清岭南画家朱美瑶的人物画中。在一套十开的《人物册》(天津博物馆藏)中,黄慎分别绘制了洛神宓妃、渊明抚琴、苏轼放鹤、漂母饭信、有钱能使鬼推磨等历史人物故事或民间传说,以及渔夫、渴饮、丝伦图、牵车、斫竹等世俗风情人物。其中《牵车》一图(图3),写一老者腰和双脚都系着绳,拉着木车,车上坐着两妇人及小孩,一妇举鞭催打着老者,一妇手托丝巾作哭泣状,两孩倚靠在车尾外侧,一孩用绳子拉着玩偶人物,一孩用绳子拉着葫芦,作玩耍状。画中葫芦,或在容器之外,也有玩具的功能。这样的画面在清代中后期的人物画中较为常见,以花鸟画擅长而兼擅人物的晚清岭南画家居廉(—)也画过一件《牵车图》(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),写一老者拉着木车,一妇人扬鞭催赶,车尾两孩自顾玩耍,车后拉着鸡犬及茶具碗筷等杂什,作者在画上题识曰:“自叹苦生涯。一个家,千觔车,筋疲力竭为牛马。儿饥叫爷,女寒叫爹,胭脂娘子鞭还骂。劝浑家,休怨咱,都是命途差。世事太纷挈,相就些,莫嗟呀。狰牙慧舌何为者,沁心有茶,养目有花,富贵荣华随他罢。力不加,肩难卸,拖得似人虾。”(图4)不难看出,此画有警世之意,似在劝喻人们淡泊名利、安然处世。若以此来解读黄慎所画,也就了然于心了。所不同者,居廉此画并无葫芦,据此可知葫芦在《牵车图》中,只是作为普通的衬景。 图5、清·朱美瑶《秋山行旅图》,纸本设色,53.2x28.4厘米,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朱美瑶的《秋山行旅图》(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)既是一幅山水画,也是一幅人物画。所绘一男士骑驴行于山麓,一书童挑担跟随其后。担子中一侧为木箱,一侧为木箱兼卷轴画、葫芦与拐杖。这是一幅常见的溪山行旅的画面,其葫芦当为容器(盛水或酒),是为长途跋涉之需。画上有禹传题跋曰:“空山皆叶落,但见点梅萼。谁耐霜雪寒,驴鞭从我著”,显示其描写的是秋冬之际的山间景致。(图5) 上述四图,是葫芦在清代人物画中最为常见的功能符号,是其自然属性的重要部分。 图6、清·黄慎《醉仙图》,纸本设色,x.5厘米,天津博物馆藏 二 在清人所绘“八仙”之一的李铁拐画像中,李仙的标准配饰几乎都为葫芦。显而易见,此葫芦是李仙的法器,具有镇妖驱魔的法力,已由自然属性转换为社会属性,是其想象性功能的重要部分。在黄慎所画的《醉仙图》(天津博物馆藏)(图6)中,李仙匍匐在硕大的葫芦上作熟睡状,葫口冒着青烟,旁有行囊及拐杖置于地上。黄慎在画中题识云:“谁道铁拐,形跛长年。芒鞋何处?醉倒华颠”,是为画面增添一注脚。此图纵横粗犷,率意为之,尺幅巨大,史载其“晚年以粗笔画仙佛,径丈许”[1],据此可知当为黄氏晚年所作。 图7、清·李育《李仙幻像图》,纸本设色,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同样的造型也出现在比黄慎略晚的扬州画家李育(—?)的《李仙幻像图》(中国国家博物馆藏)中(图7)。该图虽仅为咫尺之属的扇面,但小中见大,概可见其笔意所在。作者所写李仙在山间小憩,旁有葫芦与拐杖为伴,葫芦亦冒着缕缕青烟,环绕在李仙周围。有论者谓其“写意花卉木石,能综各家所长,脱略高浑,下笔甚捷,有心手相和、色墨并施之妙”[2],以此来观其人物,亦大致不离此道。李育长期活动于扬州,而黄慎大部分时间亦在扬州鬻画为生。两人虽然相差九十多岁,分属两个不同的时代,无缘相识,但李育应该有可能在扬州见过黄慎的相关作品并私淑其艺,故此画的构图、画风与黄氏很有相近之处。所谓的李育“能综各家所长”,“各家”之中,应包含黄慎,故在其画中,画风的一脉相承是极为明显的。尤其是葫芦的形状与青烟、李仙的形象等,都有如出一辙之感。 图8、清·沈瑶池《人物图》,纸本设色,.5x54厘米,福建博物院藏 与黄慎大致同时、且同为闽籍的画家沈瑶池(—)也有一件与黄氏画风相似的《人物图》(福建博物院藏)(图8)。虽然画名及题识并未显示画中主人为李仙,但从描绘的蓬头垢面的人物形象及配搭的葫芦看,则应是李仙无疑。图中李仙右手托蝙蝠,左手捻绳,左脚前倾,半蹲于地,一只纺锤葫芦放置于背后。所写葫芦为赭色加朱砂,再施之以淡墨,故在其粗笔的人物形象中,格外抢眼。沈瑶池在清乾隆时“征召不就,以书画终”[3],一直以布衣终老,卖画为生,其画多野逸之气。又因作者多考虑受众所需,因而在此画中,加入了蝙蝠等吉祥物,是有送“福”之意。而葫芦本身除容器、法器等功能外,亦有纳福驱邪等传说,所以名为描写李仙形象,实则别有怀抱,借此迎合艺术赞助人的审美需求了。 图9、清·李灿《人物图》,纸本设色,x50厘米,福建博物院藏 比黄慎、沈瑶池稍晚的闽籍画家李灿(—?)的一件《人物图》(福建博物院藏)(图9),也和前述诸作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李灿宗法黄慎,擅画人物、山水,尤擅绘《风尘三侠》、《李拐仙》。此图所写人物亦为李仙,作站立状,双手欲捕捉蝙蝠,腰间系一纺锤葫芦。人物的造型、笔法甚至画意都与沈瑶池等人亦步亦趋,反映出彼时大众之审美时尚。清人绘画,尤其是职业画家的作品,大多喜好对前人传移模写,画风出现程式化倾向,从黄慎、李育、沈瑶池、李灿诸家所绘李铁拐形象,便可窥其一斑。 图10、清·黄慎《骑龙图》,纸本设色,x厘米,浙江衢州博物馆藏 在黄慎的一件《骑龙图》(浙江衢州博物馆藏)(图10)中,也可见其作为法器的葫芦。所绘为一老者骑于龙之背上,腾云驾雾,后有一书童紧随其后,书童手握拄杖,杖上悬一葫芦。此处的葫芦,是老者的随身物品,本应既可是容器,亦可是法器。从画中驾驭巨龙的内容看,老者当为神道人物,故葫芦系其法器的可能性较大。 图11、清·任熊《麻姑献寿图》,纸本设色,x96.5厘米,浙江省博物馆藏 (未完待续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注释: [1]李斗撰,周春东注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二,49页,山东友谊出版社,年。 [2]蒋宝龄《墨林今话》卷十四,页,黄山书社,年。 [3]陈子奋《福建画人传》,17页,福建省博物馆印行,年。 (本文原载《文史知识》年第4、5期,收入即将出版的朱万章新著《明清书画谈丛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年9月出版) 作者简介朱万章,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研究馆员,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,中山大学特聘教授,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。从事明清以来书画鉴藏与研究、美术评论、出版、教学及展览策划等,近年研究领域开始涉及近现代美术史和当代美术评论,出版有《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》、《书画的鉴藏与市场》、《销夏与清玩: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》等论著20余种,撰写美术史与书画鉴定论文近百篇,同时兼擅书画,尤以画葫芦著称,出版有《一葫一世界:朱万章画集》、《学?艺: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》等。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luchaa.com/hlcpf/1066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落尘涂,植色染,樟树湖野放乌龙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